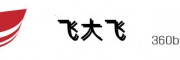3个多月前,患下咽癌晚期的孙学强,为缓解病灶带来的呼吸障碍,切开气管,接入仪器,暂得存活的手牌。
这个性格像极了名字的人,此时被抽了坚韧与强硬,瘫软在病床上,半个脑袋陷进枕头的凹槽,没有动弹。他僵化的神情仿佛能“一眼读到头”,手指开始松软,捏着的那个衣角慢慢滑动然后快速越过他不动的身体,跌进房里的寂静。
此时,靠在座椅上的孙朝晖直勾勾地盯着63岁的父亲,生怕一个转身,躲在病服里的干枯身体就会悄声“溜”走,只剩一床的褶皱和余温。
孙朝晖把自己全部的信念都塞进这间安宁病房,幻想着某天父亲的血常规正常后能继续化疗,把丢失的日子重新拉回身边。
“没有他,我就没了依靠...”
病人与家属的交流很重要
“他们应该很久没有交流了”南京鼓楼医院心理咨询师杨海龙看着这对父子,别过头,走进办公室。桌上倒压着一本欧文·亚隆的《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部分书页折起,硬生生地戳进书内。
1993年,Elizabeth Kubler-Ross 医师观察了超过200名的临终病人,总结出病人面对死亡普遍经历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纳(接纳疾病或接纳死亡)。在杨海龙多年的从医生涯中,这五阶段成为每位患癌病人的必经之路,他们或紧张、或安静、或吵闹、或哭泣,但“最后都会有这一过程。”
杨海龙需要做的就是帮助患者慢慢度过情绪变动,接受坦然疾病现状。
“第一步,我们要判别,患者的心理反应、所处时期、何种状态。”这被杨海龙称为具有决定性的“首枪”,“它会关乎下面所采用的对话方式、治疗措施以及配合几率。”
“第二步,筛选有期望的病人,推广‘安宁’理念。”杨海龙认为有选择性地对症下药,使推广不至于那么泛滥,避免激起更多状况。“大众性的宣讲,容易造成一些病人产生‘被遗弃感’,他们会认为医生护士都对我没了信心,我也看不见任何希望。”
对待这类患者,杨海龙也有自己的一套治疗模式——积极的心理介入与调整,“首先,他们所做出的每一项选择都一定是逼不得以的;其次,在选择的过程中,也会伴有情绪变化,他不知自己的选择,家属能否认同,又或者这选择对自身而言,是不是就意味着进步和改善;再者,这过程很可能不会一帆风顺,随着病程进展,患者逐渐无法正常进食、睡眠,家属也会进入抑郁时期,他们之间易发生冲突,再度引起波动。”
所以,杨海龙认为,理念的宣传与推广,一定不是告知患者已走到终点,而是希望在临近终点前的这段时间内,帮助他们唤起主动选择的愿望与可能性,能有尊严、有质量、有好的情绪状态,去获得、去选择、去维持自己的决定。
“经过心理辅导后能积极接受安宁理念的患者,在最后阶段他们的心理状态可能产生变化,生存质量反而大大提升。这过程中,家属的支持与陪伴也是不可或缺的。”
去年10月,61岁的李立明在宁馨病房走完最后旅程,安详地闭上双眼。就在两天前,身着婚纱的女儿在病房举办婚礼,让父亲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幸福地告别人世。于他而言,这份“礼物”充满了欣喜与感动。
然而,临终之“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
给杨海龙留下深刻印象的赵翔,白细胞急降,呕吐明显,不能吃喝,胃癌四期的他基本生存支持都已无法保证,但儿子依然投入大量精力、钱财,坚持治疗,“一方面,家里经济条件好,有能力供给,另一方面,害怕被说不孝顺。”
面对生死情境,这是大家都会做出的选择。“但家属的情绪反应也会影响患者。”杨海龙认为心理疏导并不是单一治疗,介入家庭层面,与家属、患者进行交流,弥补他们间失去的对话空间。
“家属明晰状况进展,患者也心知肚明,但他们已然没了沟通桥梁。患者会认为,如果说得太多,亲人只会悲观失望,他不希望将这份感受带给家人。反之,亦然。家属也深有感知,不愿和患者多谈病情。”
杨海龙认为源于某种动力的沟通交流有时会产生一种“正性情绪”,即积极、感恩、幸福的人生态度,能缓解病痛带来的不适,甚至对肿瘤可起到抑制作用。“人在孤独中,总夹杂着消失的忧愁与恐惧,如果他们间能重新建立良好沟通,也许相互的鼓气会变为有效的支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