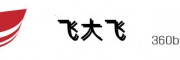从“红白杠”到普善山庄
老上海从事传统殡葬的行业叫“红白杠”,大多散布在寺庙和贳器店左近,不挂招牌但划分权力范围,担任人俗称“杠头”。“红白杠”是个松懈组织,平常杠员各行本业,遇有婚丧丧事由杠头召集,事毕即散。遇有人家办丧事,“红白杠”除代爲布置灵堂、掌管祭奠典礼、款待吊唁宾客、抬棺出殡外,还提供吃“豆腐饭”所需的炊饮餐具及桌椅板凳等。
这些用具多由“红白杠”出面向贳器店租赁,所以“红白杠”与贳器店构成“一条龙”效劳。所谓贳器店,是指专门出租祭奠和餐饮用具的店家,这些用具多用于红白丧事,包括茶担、圆桌等。有时应客户要求,贳器店也提供诸如搭天棚、扎彩、挂堂幔、张挽幛等效劳。老上海的贳器店多集中在黄浦区的永寿路上,故当年有“贳器一条街”之称。
百年前的上海还处在“以轿代步”的时代,无论文文官员出巡,还是富豪乡绅出游,其交通工具多爲轿子。主人位置越显赫,轿夫就越多。所以那时有钱人家出殡,都要叫上一帮“红白杠”组成轿班,抬着覆以帐幔的楠木棺材巡游一周后,再到墓地落葬,或停厝寺庙庵堂内。此举无非是摆阔、讲排场而已。 与此同时,上海又是个移民城市,当年沪上众多同乡会馆、公所的次要任务,就是爲客死同乡提供场所以暂厝棺柩,待日后运葬故里,此外还向贫穷同乡施恤棺木,辟建义冢地埋葬遗体。这些厝柩的场所称之爲丙舍或寄柩所。上海最早的丙舍当推四明公所于1798年(清嘉庆三年)在老城厢北门外设立的寄柩厂。“厂”址位于古人民路852号,当年占地30余亩,由旅沪宁波籍人士每人每天捐助一文钱集资购地建造。
与此同时,上海又是个移民城市,当年沪上众多同乡会馆、公所的次要任务,就是爲客死同乡提供场所以暂厝棺柩,待日后运葬故里,此外还向贫穷同乡施恤棺木,辟建义冢地埋葬遗体。这些厝柩的场所称之爲丙舍或寄柩所。上海最早的丙舍当推四明公所于1798年(清嘉庆三年)在老城厢北门外设立的寄柩厂。“厂”址位于古人民路852号,当年占地30余亩,由旅沪宁波籍人士每人每天捐助一文钱集资购地建造。
此外还有诸如普善山庄和同仁辅元堂这样的慈悲集团,用募集到的善款辟建义冢地,以埋葬、火化倒毙街头的“露尸”。另设有施材栈,向贫穷死者收费提供棺木。当年设在江宁路上的普善山庄施材栈常年消费刷有蓝底白十字标志的薄皮棺材,并在江宁路桥北堍左近建有义冢地,在成都路桥南堍辟筑露尸火葬场。1937年中国战机误炸大世界难民所,炸死2000余人。普善山庄收尸车全体出动,又租借多辆卡车至现场拾掇残骸,两天后才清算终了,尸骸运往大场公墓掩埋。至于同仁辅元堂的义冢地,大多散布在浦东白莲泾一带。
美国老板的生意经
近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国际性大都市,随着外侨不时涌入,客死沪上者自然也同步添加。这些本国丧家已不满足先前次要由教堂掌管的葬礼,希望能有一家专门机构爲其提供殡葬效劳。1926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华凯斯柯特公司瞄准商机,向一位旅沪法国侨民租下了位于今胶州路207号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创办了专事殡殓的“大礼厅”,次年改称“万国殡仪馆”。自此“殡仪馆”三字才爲国人所承受,而万国殡仪馆成爲上海第一家正轨殡仪馆。
1934年时任经理的美国人施高德将万国殡仪馆改组爲独资企业,自任老板,同时承办“初等”华人丧事,除提供汽车接尸,防腐整容,著衣成殓,存放棺柩,协助办理土、火葬等惯例效劳外,还自制棺材及骨灰盒出售,并在馆内专设壁龛,供存放骨灰之用。听说当年馆内备有两辆美国造的“克雷斯莱”牌轿车,其中大轿车车身较长,专门用于接送遗体。至于那辆小轿车由施高德公用,他经常开着小车亲临丧家,一探真假。遇有殷商大户,这位美国老板便大献殷勤,竭力引荐各类高档丧葬用品,抬高殡殓规格,爲的是掏尽丧家腰包。
万国殡仪馆的底层礼厅原来全爲西式装饰,内置钢琴一架。外侨丧礼由神父或牧师掌管,唱诗班在钢琴伴奏下齐唱赞誉诗《地狱再相会》,以示送魂入地狱。自施高德独掌该馆后,遇华人丧事亦允许在西式礼厅内吹打中国民乐,大做水陆道场。在当年的“万国”洋房花园中,经常可见袅袅香烟随同着悠悠丝竹谐和喃喃诵经声飘向远方……而这些超度的亡灵给施高德带来的却是丰厚的报答,听说当年万国殡仪馆每月只需承办一两家丧事,即可维持当月日常开支,若多来几家则爲纯利矣。
1935年阮玲玉灵柩从万国殡仪馆运往安葬途中
1935年因吊唁阮玲玉的民众络绎不绝,施高德心血来潮,宣布吊丧者必需身佩小黄花,每朵小花售价一元。试想一下,开吊三天,祭奠者达十万之众,施高德的腰包又该鼓胀几许? 抗战中勃兴“经济型”殡仪馆
抗战中勃兴“经济型”殡仪馆
随着万国殡仪馆的创办,这种古代化的殡殓机构逐步爲沪上“开习尚之先”人士所承受,至抗战迸发前,国人自办的殡仪馆已有中国、上海、地方三家。1937年抗战迸发,民众纷繁避难“孤岛”租界,界内人口激增,房屋充足,升斗小民遇有丧事,往往就在弄堂里露天殡殓。又因和平关系,会馆公所原先承办的寄柩、运葬业务大多进展,因无处停厝,棺柩经常被放置在人行道上,严重危及公共卫生。
于是,在沪西及南市地域相继呈现了以“取费昂贵,手续简便”招徕丧家的“经济型”殡仪馆,沪西有群众、乐园、万安、世界、大华、白宫、上天、大陆、安乐等近十家;南市有沪南、南市、斜桥、永安、丽园、国际等数家;虹口唐山路上开有国华殡仪馆。至束缚前夕,上海共有大小殡仪馆约30家,私营寄柩所24家。至此,上海私营殡葬业达一高峰。
这些殡仪馆次要从事接尸、整容、入殓、寄柩等业务,兼售寿材、寿衣等丧葬物品,有的还协助办理运柩、公墓落葬、筵席贳器,代请僧尼、道士等。一般殡仪馆还采用冷气或注射防腐针方式保管遗体。但八年抗战,交通阻滞,存放于各殡仪馆内的棺柩因无法及时清运,堆积如山。一朝一夕,棺木破败,腐水外泄,秽气冲天,所谓“积柩成绩”再次危及市民身心安康。
抗打败利伊始,上海市政府曾严令各殡仪馆限期出清积柩,并不得再行寄柩,逾期全部火化。这条命令不啻给大小殡仪馆一个繁重打击,须知他们是专靠售材、寄柩赢利的。有位殡仪馆老板就曾感慨道:“殡仪馆的钱太好赚了!每年光寄柩费一项便有几亿元支出。此外代买寿材也有丰厚利润,越是想买好棺材的有钱人,钱越好赚,可以漫天开价。”结论是:“开过殡仪馆后,什麼生意都不想做了!”好在不久内战迸发,国民党当局应对的危机远比“积柩”严重,也就无意“肃清积柩,厉行火葬”了。
上海束缚后,人民政府着手肃清各类积柩、浮厝达10万具之多,并积极推行“倡导火葬、限制土葬、鼓舞外运”的殡葬变革政策。一向靠寄柩、售材牟利的私营殡仪馆在新政权的威势下,自然是客户大减、营业萎缩,纷繁歇业或转产,残存者也在1956年的公私合营浪潮中并入公营殡葬单位。
老上海从事传统殡葬的行业叫“红白杠”,大多散布在寺庙和贳器店左近,不挂招牌但划分权力范围,担任人俗称“杠头”。“红白杠”是个松懈组织,平常杠员各行本业,遇有婚丧丧事由杠头召集,事毕即散。遇有人家办丧事,“红白杠”除代爲布置灵堂、掌管祭奠典礼、款待吊唁宾客、抬棺出殡外,还提供吃“豆腐饭”所需的炊饮餐具及桌椅板凳等。
这些用具多由“红白杠”出面向贳器店租赁,所以“红白杠”与贳器店构成“一条龙”效劳。所谓贳器店,是指专门出租祭奠和餐饮用具的店家,这些用具多用于红白丧事,包括茶担、圆桌等。有时应客户要求,贳器店也提供诸如搭天棚、扎彩、挂堂幔、张挽幛等效劳。老上海的贳器店多集中在黄浦区的永寿路上,故当年有“贳器一条街”之称。
百年前的上海还处在“以轿代步”的时代,无论文文官员出巡,还是富豪乡绅出游,其交通工具多爲轿子。主人位置越显赫,轿夫就越多。所以那时有钱人家出殡,都要叫上一帮“红白杠”组成轿班,抬着覆以帐幔的楠木棺材巡游一周后,再到墓地落葬,或停厝寺庙庵堂内。此举无非是摆阔、讲排场而已。
 与此同时,上海又是个移民城市,当年沪上众多同乡会馆、公所的次要任务,就是爲客死同乡提供场所以暂厝棺柩,待日后运葬故里,此外还向贫穷同乡施恤棺木,辟建义冢地埋葬遗体。这些厝柩的场所称之爲丙舍或寄柩所。上海最早的丙舍当推四明公所于1798年(清嘉庆三年)在老城厢北门外设立的寄柩厂。“厂”址位于古人民路852号,当年占地30余亩,由旅沪宁波籍人士每人每天捐助一文钱集资购地建造。
与此同时,上海又是个移民城市,当年沪上众多同乡会馆、公所的次要任务,就是爲客死同乡提供场所以暂厝棺柩,待日后运葬故里,此外还向贫穷同乡施恤棺木,辟建义冢地埋葬遗体。这些厝柩的场所称之爲丙舍或寄柩所。上海最早的丙舍当推四明公所于1798年(清嘉庆三年)在老城厢北门外设立的寄柩厂。“厂”址位于古人民路852号,当年占地30余亩,由旅沪宁波籍人士每人每天捐助一文钱集资购地建造。此外还有诸如普善山庄和同仁辅元堂这样的慈悲集团,用募集到的善款辟建义冢地,以埋葬、火化倒毙街头的“露尸”。另设有施材栈,向贫穷死者收费提供棺木。当年设在江宁路上的普善山庄施材栈常年消费刷有蓝底白十字标志的薄皮棺材,并在江宁路桥北堍左近建有义冢地,在成都路桥南堍辟筑露尸火葬场。1937年中国战机误炸大世界难民所,炸死2000余人。普善山庄收尸车全体出动,又租借多辆卡车至现场拾掇残骸,两天后才清算终了,尸骸运往大场公墓掩埋。至于同仁辅元堂的义冢地,大多散布在浦东白莲泾一带。
美国老板的生意经
近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国际性大都市,随着外侨不时涌入,客死沪上者自然也同步添加。这些本国丧家已不满足先前次要由教堂掌管的葬礼,希望能有一家专门机构爲其提供殡葬效劳。1926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华凯斯柯特公司瞄准商机,向一位旅沪法国侨民租下了位于今胶州路207号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创办了专事殡殓的“大礼厅”,次年改称“万国殡仪馆”。自此“殡仪馆”三字才爲国人所承受,而万国殡仪馆成爲上海第一家正轨殡仪馆。
1934年时任经理的美国人施高德将万国殡仪馆改组爲独资企业,自任老板,同时承办“初等”华人丧事,除提供汽车接尸,防腐整容,著衣成殓,存放棺柩,协助办理土、火葬等惯例效劳外,还自制棺材及骨灰盒出售,并在馆内专设壁龛,供存放骨灰之用。听说当年馆内备有两辆美国造的“克雷斯莱”牌轿车,其中大轿车车身较长,专门用于接送遗体。至于那辆小轿车由施高德公用,他经常开着小车亲临丧家,一探真假。遇有殷商大户,这位美国老板便大献殷勤,竭力引荐各类高档丧葬用品,抬高殡殓规格,爲的是掏尽丧家腰包。
万国殡仪馆的底层礼厅原来全爲西式装饰,内置钢琴一架。外侨丧礼由神父或牧师掌管,唱诗班在钢琴伴奏下齐唱赞誉诗《地狱再相会》,以示送魂入地狱。自施高德独掌该馆后,遇华人丧事亦允许在西式礼厅内吹打中国民乐,大做水陆道场。在当年的“万国”洋房花园中,经常可见袅袅香烟随同着悠悠丝竹谐和喃喃诵经声飘向远方……而这些超度的亡灵给施高德带来的却是丰厚的报答,听说当年万国殡仪馆每月只需承办一两家丧事,即可维持当月日常开支,若多来几家则爲纯利矣。
1935年阮玲玉灵柩从万国殡仪馆运往安葬途中
1935年因吊唁阮玲玉的民众络绎不绝,施高德心血来潮,宣布吊丧者必需身佩小黄花,每朵小花售价一元。试想一下,开吊三天,祭奠者达十万之众,施高德的腰包又该鼓胀几许?
 抗战中勃兴“经济型”殡仪馆
抗战中勃兴“经济型”殡仪馆随着万国殡仪馆的创办,这种古代化的殡殓机构逐步爲沪上“开习尚之先”人士所承受,至抗战迸发前,国人自办的殡仪馆已有中国、上海、地方三家。1937年抗战迸发,民众纷繁避难“孤岛”租界,界内人口激增,房屋充足,升斗小民遇有丧事,往往就在弄堂里露天殡殓。又因和平关系,会馆公所原先承办的寄柩、运葬业务大多进展,因无处停厝,棺柩经常被放置在人行道上,严重危及公共卫生。
于是,在沪西及南市地域相继呈现了以“取费昂贵,手续简便”招徕丧家的“经济型”殡仪馆,沪西有群众、乐园、万安、世界、大华、白宫、上天、大陆、安乐等近十家;南市有沪南、南市、斜桥、永安、丽园、国际等数家;虹口唐山路上开有国华殡仪馆。至束缚前夕,上海共有大小殡仪馆约30家,私营寄柩所24家。至此,上海私营殡葬业达一高峰。
这些殡仪馆次要从事接尸、整容、入殓、寄柩等业务,兼售寿材、寿衣等丧葬物品,有的还协助办理运柩、公墓落葬、筵席贳器,代请僧尼、道士等。一般殡仪馆还采用冷气或注射防腐针方式保管遗体。但八年抗战,交通阻滞,存放于各殡仪馆内的棺柩因无法及时清运,堆积如山。一朝一夕,棺木破败,腐水外泄,秽气冲天,所谓“积柩成绩”再次危及市民身心安康。
抗打败利伊始,上海市政府曾严令各殡仪馆限期出清积柩,并不得再行寄柩,逾期全部火化。这条命令不啻给大小殡仪馆一个繁重打击,须知他们是专靠售材、寄柩赢利的。有位殡仪馆老板就曾感慨道:“殡仪馆的钱太好赚了!每年光寄柩费一项便有几亿元支出。此外代买寿材也有丰厚利润,越是想买好棺材的有钱人,钱越好赚,可以漫天开价。”结论是:“开过殡仪馆后,什麼生意都不想做了!”好在不久内战迸发,国民党当局应对的危机远比“积柩”严重,也就无意“肃清积柩,厉行火葬”了。
上海束缚后,人民政府着手肃清各类积柩、浮厝达10万具之多,并积极推行“倡导火葬、限制土葬、鼓舞外运”的殡葬变革政策。一向靠寄柩、售材牟利的私营殡仪馆在新政权的威势下,自然是客户大减、营业萎缩,纷繁歇业或转产,残存者也在1956年的公私合营浪潮中并入公营殡葬单位。